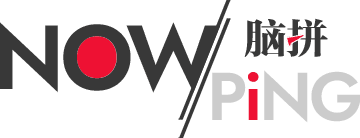在时代激流中,如何避开向下的沉沦
在灾难频仍、祸患丛生的世界生存,我们需要一个榜样或路标。这个榜样和路标不仅可以令我们汲取思想的力量,还可以使我们内心镇定、精神稳固,避开向下的沉沦。
文/夏榆
1. 时代的忧惧
“生命的忧惧与每件事都摆脱不了关系。所有的犹豫不定都沾染上了忧惧的成分,除非我们能忘掉忧惧。牵挂使我们无所适当地保护自己的生命。那种过去相当普遍但不受指责的残酷行为,已经比以前少见了,但是我们发现,那些目前仍然存在的残酷暴行却似乎比以往更加恐怖。”
这段关于忧惧的语句出现在卡尔·雅斯贝尔斯的著作《时代的精神处境》,我在54页用笔画上虚线着重阅读,这是第三节“群众秩序与生活间的紧张”的表达内容,包括它的小标题“生命的忧惧”,可以与当下的人类生活图景形成观照与呼应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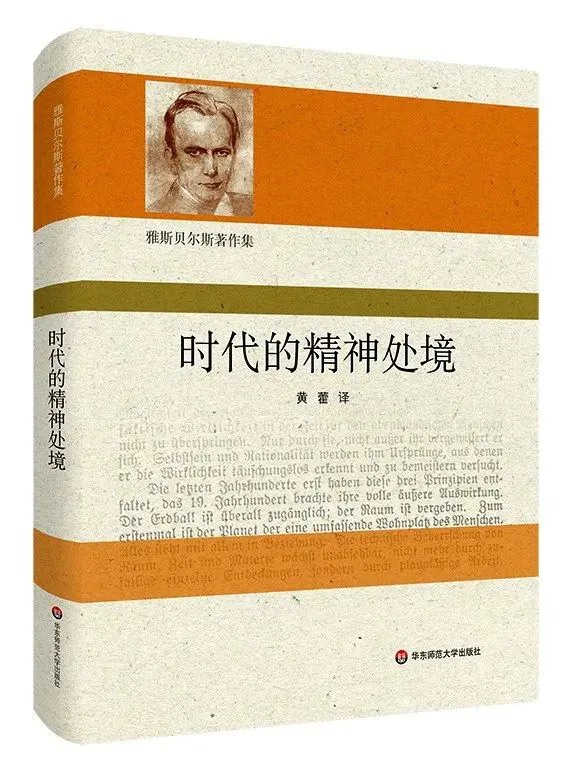
近年来读雅斯贝尔斯渐多,最初引领我走向雅斯贝尔斯的是切斯瓦夫·米沃什,在那本著名的《被禁锢的头脑》中,雅斯贝尔斯撰写了序,谈到他经历过的极权主义时代的国家状态。“我们德国人突然发现自己身居牢笼之中”,1930年,雅斯贝尔斯思考着他所看到的政治灾难的前兆,大学教育的纳粹化,国家思想支配着大学权力,近乎疯狂的庸众对法西斯的狂热。
《时代的精神处境》不仅是对政治现状的分析,而是“对我们时代全部的道德、精神状况的分析”。二十世纪的灾难验证了这位哲学家的远见,检测了他思想的恒久生命力。
“有关时代境况的问题,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变得愈加重要,而每一世代都尽力想要根据自己的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雅斯贝尔斯在《时代的精神处境》的绪论中写道。1931年,他在德国知识界崭露头角,先是《时代的精神处境》完成,接着三卷本的《哲学》问世,然后是关于马克斯·韦伯的论著,这些著作的出版使他成为公众人物。
《时代的精神处境》是对1920年—1930年经济大萧条年代以及魏玛共和时代的德国社会所做的观察、诊断、反思与描述。1951年雅斯贝尔斯在英译本的新序言里写道:“本书1930年写成,当时我对纳粹党一无所知。当纳粹于1930年9月大选初次获胜时,我感到讶异与震惊。……为了照亮那个时代,我运用了属于那些特殊年代里的事实,在许多方面使该书拥有时代的氛围。”
我也在英国作家莎拉·贝克维尔所著《存在主义咖啡馆》里与他相遇,在这部563页的有轻逸文笔也有严肃哲学思想的文本里,重现了二十世纪哲学大师们的人生场景,刻画了思想者的肖像,描述了思想者的旅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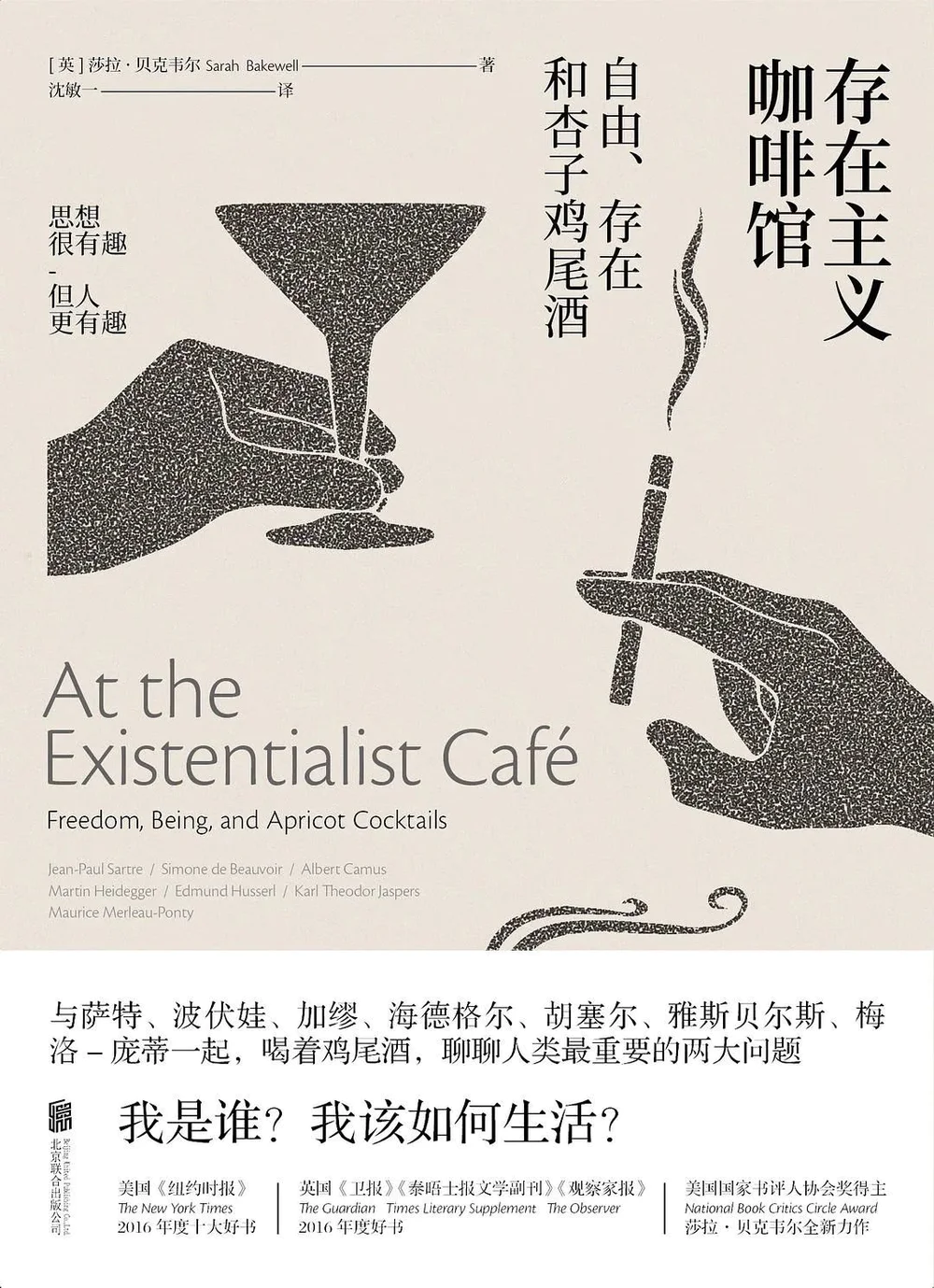
萨特在巴黎沦陷于纳粹铁蹄之下的战俘营里坚持写日记,这些日记后来成为他的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的文本基础;加缪在沦陷的巴黎坚持他的文学和戏剧写作,完成后世称为经典之作的《异乡人》《反抗者》《瘟疫》,同时参加反纳粹的抵抗者运动;还有雅斯贝尔斯与他同时代的哲学巨匠海德格尔和汉娜·阿伦特之间的交往。
之后我又在《海德格尔传》以及《汉娜·阿伦特:爱这个世界》中再次与雅斯贝尔斯重逢。在这些书籍里,永久留存着思想家的生命场景以及他们的精神旅程,不同时代的灾难、祸患、创伤与危机也都闪现其间。
鲜明的时代巨变令人类与存在的终极问题重逢,二十世纪的思想家们是我愿意寻找和阅读的,不仅因为他们经历过那个世纪连绵的灾难,还因为在时空上距离我们更近。我有了解这些杰出者的好奇,看他们如何在动荡和恐怖的时代生活,又如何在灾难和离乱中思想和写作。
2. 人的精神境况在时间的河流中
雅斯贝尔斯所在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相隔百年,然而时代的严峻性依然是同一的——依旧有全球瞩目的战争,强国对弱国的吞并和征服——只是杀戮的规模更大,精确制导的导弹取代火炮,取代人肉搏杀;依旧是意识形态的攻伐,文明与野蛮的对垒。人心对恐惧、疑难和困境的体验并无实质改变。
在《时代的精神处境》里,雅斯贝尔斯阐述了时代意识的起源,展现出广阔的思想视野。他深入到人类存在的实况去观察和解析,对不同的面向进行形而上的思辨。
读到这样的思考,你会感觉它穿越时间的力量:“在生活秩序的合理化与普遍化的过程中,与某种不可思议的成功同时出现的,是一种大难来临的意识,这种意识也就是一种对一切生命价值即将毁灭的忧惧。不仅社会体制在改造的过程中似乎预示了一切都将毁灭之兆,甚至体制本身也受到威胁,一种怪异的情况因此产生,一方面,人无法离开社会体制而生存,另一方面,不管体制本身是改进还是瓦解,二者同时显示对人类具有毁灭性。”
《时代的精神处境》对我来说是一部安慰之书。当我们身处动荡剧变的时代激流,眼见世界在失序中滑翔,残酷成为人类社会的真实图景,打开雅斯贝尔斯的书,你可以看到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对存在的深邃思考,对现实和历史的应对之法,你发现他的思想并没过时。
人并非需要哲学生活,然而却需要思考生活。“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一过。”苏格拉底如是说。这句话出自柏拉图的《申辩篇》,苏格拉底通过对话表达了对生活的看法,强调审视和思考在人生中的重要性。
在灾难频仍、祸患丛生的世界生存,我们需要一个榜样或路标。这个榜样和路标不仅可以令我们汲取思想的力量,还可以使我们内心镇定、精神稳固,避开向下的沉沦。
雅斯贝尔斯是经受住时代考验的知识分子。1930年代希特勒领导的纳粹政权崛起,与同在海德堡大学担任教职的哲学家海德格尔附逆纳粹不同,雅斯贝尔斯因为妻子格尔特鲁德是犹太人,也因为他所持的自由价值观和独立学术立场,被排除出海德堡大学的管理机构,他被免去教职,禁止发表出版作品。
雅斯贝尔斯不愿受到纳粹暴力的凌辱,不愿意被关押到集中营。为应付最危急的情况,他保留着“最后的避难所——自杀”。他通过当医生的朋友弄到自杀的药物,这些药白天放在橱中,夜间放到床头柜上,盖世太保说不准哪天一清早就来。他写就医嘱并设法购置一块可以埋葬全家人的墓地,他在医嘱里写道:“我代表我们俩声明,我们不希望抢救;相反,如果死亡没有立即降临的话,我们恳求采取无痛致死的措施。”
所幸雅斯贝尔斯等到了最后的解放,1945年他和妻子将被遣送到集中营。3月30日,海德堡被美军占领,他们夫妇逃脱被押遣的厄运。1948年雅斯贝尔斯应邀到巴塞尔担任教职,吸引他的是“政治自由、欧洲的辽阔以及布克哈特、尼采和欧文贝克的精神”。
有段时间我出门到咖啡馆闲坐,都会随身带《雅斯贝尔斯》,一本32开本的小书。这本书与《时代的精神处境》对照阅读令人更能体会穿越时间的智识之光。“哲学所必须照亮的地方”,雅斯贝尔斯借用克尔凯郭尔的语汇写道:“此在、生存、超越、意识、临界情况、交往、失败、严酷。”
这些书数不清读过多少遍,每次读都有欣悦和激赏感。我在阅读札记中写道:“雅斯贝尔斯,恐怖时代的道德标杆,灾难之年的人格典范。”
3. 在生命中检验自身
《时代的精神处境》这部写于1932年的书在面世之后不断再版,走向一代又一代新的读者。时间流逝,时代的风貌在改变,然而人在时代中的精神境况却亘古未变,如雅斯贝尔斯所写:“哲学生活,就像一阵流星雨,无数的陨石,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却在生命的天际划过。”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类生活在一个日新月异的年代,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使资讯像汪洋涌来,淹没覆盖着人类心灵。人的精神性逐渐被忽视,个人的真知在丧失,失去精神性依靠的人类成为盲从权力和资本的庸众。现代技术放大人的声音,这庞杂的声音夹杂着更多不良的讯息;仇恨及反人类意识无限制传播,反智主义甚嚣尘上。
印度国父甘地认为有7种行为可能毁灭人类,这警诫对现代人依然有效,它们分别是:没有伦理的政治、没有辛劳的财富、没有人格的学识、没有人性的科学、没有道德的商业、没有良知的享乐、没有牺牲的崇拜。阅读的奇妙在于,经由我们的存在、介入、在场,连接了逝去多年的杰出生命,这个生命与另一个更为杰出的生命相互连接,他们从历史云烟中浮现而出,语言及言辞重获生命。
我的案头书除了《时代的精神处境》,还有雅斯贝尔斯的多部著作(《给青年人的哲学十二讲》《四大圣哲》)。他的哲学思考深入存在的不同维度,聚焦人类生活的历史和现实。他的著作——包括没有进入中文世界的《现代的人》《德国罪行问题》《原子弹与人类未来》——都始终保持着智识的敏感和深度。1958年雅斯贝尔斯获德国书业和平奖时,他的学生同时也是终身挚友的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颁奖仪式上发表了致辞《卡尔·雅斯贝尔斯:一篇赞词》:
他是彻底独立的,不依靠任何群体,包括德国抵抗运动在内。这一立场完全由人格力量来支撑,它的高贵正好在于:即使在极权主义的黑暗中,他也不会去代表任何事物,而只为自身的生存提供确证。而在这种黑暗中,善即使仍然存在,也变得绝对不可见并因而无效了——甚至理性都可以被消灭,假如所有具备理性的人类真的被杀掉了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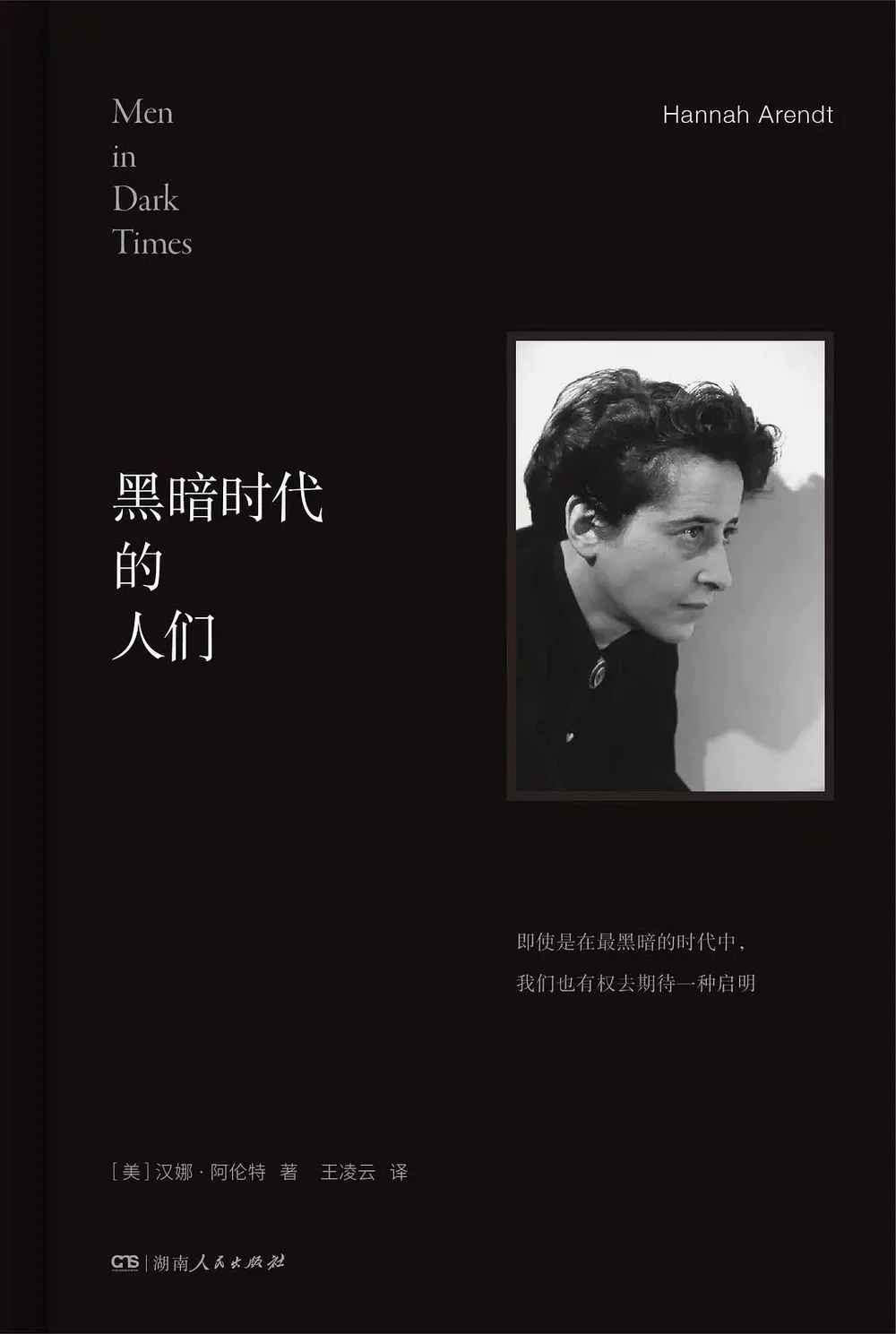
“在其生命中对自身的检验”,阿伦特对雅斯贝尔斯的赞词可以作为我们对自身的眺望。这篇演讲辞收入在阿伦特的文集《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代哲学巨匠的阿伦特对她的老师兼挚友的人格鉴识也是我在今天致敬雅斯贝尔斯的缘由:
他在灾难期间仍然很坚强。然而,可能不那么明显的是,这整个灾难事件从来都不能诱惑他放弃人性——这就是他的不可冒犯之处,这意味着比抵抗和英雄主义重要得多的东西。它意味着一种无须证明的信心,意味着一种确信:在一个什么都可能发生的时代中,有一件事绝不会发生。雅斯贝尔斯是完全独立的,他所代表的并不是德国人,而是德国人仅存的humanitas。就仿佛他独立于凛然不可冒犯之中,便能照亮由理性在人们之间创造和维护的空间;就仿佛只要一个人还在,这一空间的明亮和广阔就能存在下去。
- 来源:经观书评
- 原标题:《在时代激流中保存人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