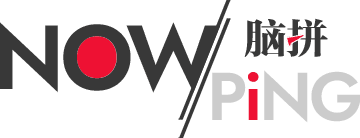《花样年华》四分之一个世纪:电影里爱情可以永远保鲜
文/余雅琴
“花重开,胜如旧。不一样的久别重逢。”2025年2月,导演王家卫发了一条这样的微博。几天后的情人节,他的名作《花样年华》于中国内地重映,这一次上映的版本以“特别版”命名,号称历史最长版,一共103分钟。不但加入了未公开过的5分钟全新内容,还承诺这个版本只能在院线看到。
几天后,王家卫又释放出一条与AI对话的视频。这一次AI“化身”一位与《花样年华》同龄的25岁女性,“她”就这部电影重映的意义和王家卫进行了讨论,王家卫说,这次上映的版本事实上更接近自己最初的想法。
“这是典型的‘墨镜王’的行事风格。”一位资深影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们早就对他类似的操作不陌生了,就连发行DVD他都可以搞好几个版本,也总有人喜欢考据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
虽然已经有超过十年没有电影新作推出,但近年来王家卫的作品不断有新版本在内地院线公映,从《东邪西毒》终极版、《一代宗师》3D版、《阿飞正传》数字修复版,到这次的《花样年华》特别版,王家卫绝对算得上电影圈的“版本学”大师。

在华语地区的大导演里,王家卫是有名的低产,从1988年拍摄首作《旺角卡门》以来,他一共只导演了十部电影长片,且大部分都完成在1990年代。2013年,王家卫的《一代宗师》上映后,他就专心投入了剧集《繁花》的筹备和制作,再没有新的长片推出。
但这并不意味着王家卫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或许放眼整个华语地区,也没有哪位导演会如他一般,一举一动都会被影迷关注和解读。有时候,哪怕仅仅是转发抑或点赞了一条微博,也会引发影迷的持续讨论,说他是电影导演里的“流量明星”也不过分。
回顾王家卫的成名历史,“晦涩难懂”曾经是一个高频的形容词,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他电影的喜爱。探究其中的原因,除了他总是擅长挖掘大牌明星潜藏的魅力之外,恐怕也因为他对影像的唯美化追求,在王家卫的电影里,日常生活总能迸发出一种超现实的美感,哪怕是《花样年华》中男女主角吃的云吞面。
在王家卫的作品序列中,《花样年华》的地位尤其特殊,它的大众知名度和国际声誉都不容小觑。《花样年华》不但激发了电影评价体系对东方电影美学的热情,也引领了时尚界一股东方情调的复古风。对于彼时的中国内地影迷来说,《花样年华》是伴随着“小资情调”进入视野的,它的背后也蕴含着一场生活方式的革新。
尤其难得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花样年华》的影响力不但没有衰退,还在持续地经典化。英国的BBC将其评为“21世纪最伟大百部电影的第二位”;《视与听》杂志则将它列为影史五十部佳片之一;至于一贯以严苛著称的法国《电影手册》杂志也在2015年将其评为影史250部佳作的唯一华语电影。
截至发稿前,《花样年华》特别版在上映13天后取得了5324万元的票房成绩,这在一部重映电影中实属难得。
三个不一样的结局
《花样年华》提供了一种通俗意义上的怀旧情调,其中很多场景复刻了王家卫的童年记忆,作为上海移民的后代,他在女主角苏丽珍身上也投射了自己对母亲的印象。这部电影的片名来自周璇的同名歌曲,一下就把观众拉入了某种对旧日时光的想象。
电影的灵感来自香港文学大家刘以鬯的小说《对倒》。尽管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但《对倒》的结构、氛围和情调,都深深地影响了王家卫,他将小说中的部分金句以字幕卡的形式放进了电影中。
最初,王家卫想要拍摄一部名为“三个关于食物的故事”,打算以1960年代的电饭锅、1970年代的方便面和2000年的便利店这三个与吃饭相关的故事,展现不同时代的男女关系。他先是拍摄了2000年的部分,后来就开始着手于1960年代的故事,结果越拍越长,最后干脆推翻了之前的构想,拍出了《花样年华》。
电影中的苏丽珍是香港最早的一批职业女性,她没有像那个时代大部分主妇那样相夫教子,而是选择了外出工作,虽然仅仅是一家小公司的秘书。她在公司被人叫做“苏秘书”,回到日常生活则被人叫做“陈太太”,唯独没有人叫她的名字。
苏丽珍能够在社会上获得一席之地,背后得益于诸如电饭锅这样的家电发明,部分地解放了这代女性的家务压力。但天不遂人愿,经济的独立并不意味着家庭生活的平等,苏丽珍发现丈夫和女邻居出轨偷情,陷入了持续的痛苦,也开始寻求与女邻居的丈夫——也就是片中男主角周慕云的情感安慰。
对于大部分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来说,他们最难忘的部分就是王家卫对这段“越轨”感情的处理,他将东方式的“发乎情,止乎礼”发展到极致,一对男女在斗室之中情感极限拉扯,但终究没有越雷池一步。电影的最后,一对相爱的男女分开又错过,彼此思念,但再也没有相见,可以说将所谓的“BE(Bad Ending)美学”发挥到极致,给人留下无限的怅惘和遗憾。
在《花样年华》诞生至今的25年里,王家卫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地释放关于这部电影未公映的其他可能性,在他最初的构想中,男女主人公曾经突破了礼数发生过亲密关系,也在分开多年后有过一次重逢……这些最终版本没有呈现出来的细节让观众对《花样年华》有了更多方向的解读,比如苏丽珍多年后单身带着一个名为庸生的孩子,就被认为这个名字的灵感来自金庸和梁羽生,既是女主角对两个人过去一起写武侠小说的纪念,也暗示了孩子的父亲可能是周慕云。
对于一般的电影来说,这些可能性或许无关紧要,但对于“细节控”王家卫来说,在电影里设置谜题邀请观众寻找答案是一种常态。因此,在“重映版”公映之前,关于这部电影各个版本的传闻又流传开来,除了诸如剧情上的改动,还有调色光影的微妙变化,都成为再次解读这部电影的切入口。
当然,电影最终的呈现并没有颠覆原本的叙事,除了加入了一段五分钟左右的发生于2000年的便利店故事之外,《花样年华》特别版没有改变原来的故事走向。但恰恰又是这多出来的五分钟,让今天的观众对这部电影有了一种新的解读。在2000年的故事中,当代的苏丽珍和周慕云一个化身神秘的都市女郎,一个则是便利店老板,前者和恋人分分合合,分手的时候就把钥匙放在便利店,时间长了,两个人产生某种情愫,男方趁着女方熟睡,勇敢地亲吻了她,电影也就此定格……
这五分钟很容易让人想起王家卫的另外一部电影《蓝莓之夜》,可以说轻盈又浪漫,它同时也给出了男女主角在当代生活的可能性。正如王家卫在和AI的对话中所说的那样:“如果两个人的爱情发生在今天,结果肯定会不同。”
本来,电影最后的吴哥窟场景,王家卫的确设置了两个人的重逢,在这个版本中,苏丽珍回归了家庭,两个人只当从前的事情没有发生,告别之际,周慕云问她是否曾给自己打过电话,苏丽珍愣住片刻,笑着说“我不记得了”。在电影正式上映前,王家卫把这个结尾拿掉了,他想给苏丽珍另外追求自由的可能性,电影改为她带着孩子独自生活,也成就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拥有许多语焉不详秘密的版本。
时隔25年之后,王家卫在微博上公开了吴哥窟重逢这段的高清修复版本,也给出了观众对《花样年华》这部电影的又一个解读空间。而这些创作过程中的取舍,蕴含的不仅仅是王家卫对叙事节奏的把控,也体现着电影内外女性意识变化的流动。正如2025年的今天,年轻的观众开始热络地在小红书上讨论苏丽珍不应该回归家庭的话题,敏感如王家卫,早在创作之初就已经意识到这种人心的浮动。

或许,1960年代的香港社会本来就处在新旧的剧烈冲突中,潘迪华饰演的房东太太操着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在衣食住行上处处保持着上海的习惯,关起门来假装一切都没有变;而年青一代,早就在外出工作,不遵循婚姻的诺言,以及在冷漠的邻里关系中走向了无所谓好坏,但不得不改变的现代社会。
一部关于“秘密”的电影
王家卫说,他拍摄《花样年华》从来不是因为这是一个“出轨”的故事,而是关于“秘密”,他想知道那时候的人们如何保守内心的秘密。周慕云和苏丽珍最初的接触是为了弄明白伴侣为何会背叛自己,为此甚至开始了角色扮演的游戏,希望接近伴侣的内心。但当他们也产生了某种情愫后,才终于明白“原来很多东西不知不觉就来了”。
电影的最后,周慕云来到了柬埔寨吴哥窟,将自己不能宣之于口的恋情对着一个洞穴讲述了出来,再把它用泥巴封住。远处,只有一个少年僧侣看到了这一切,镜头再拉远,吴哥窟纹丝不动。
在这里,王家卫特别使用了一段历史影像片段。那是1966年,法国的戴高乐总统访问柬埔寨,当时他发表了谴责越战的言论,也标志着柬埔寨殖民时代的结束。这里乍看像是一处闲笔,却在最后提示观众一个重要的信息:在这场美轮美奂的东方爱情发生的背后,在男女主角摇曳荡漾的内心之中,存在着一个怎样动荡的年代。
按照这个脉络来看,电影中的相逢、试探、相爱和分别,其实也都有一条历史的隐形线索,可以窥见上世纪中叶华人移民的离散往事。电影中,周慕云问苏丽珍,如果自己多一张船票,她会不会和他一起走。留下还是离开,不仅困扰着这对恋人,也是很多人反复思考的问题。
2020年,主演张曼玉和梁朝伟曾在加拿大多伦多电影节宣传《花样年华》,在记者发布会上,张曼玉也被问到如何理解电影的最后一部分。她提到,电影就像一个显微镜,观察这个世界的尘埃,在显微镜的作用下,这两个人显得很重要,但在历史上却没有意义。电影直到结尾处才把镜头拉远,告诉我们世界其实很大,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发生,在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事情很小,也很个人。
在《花样年华》之前,王家卫主要和摄影指导杜可风合作,后者擅长拍摄手持镜头,在他此前的名作《东邪西毒》《重庆森林》《春光乍泄》等中很擅长用运动的镜头去表达现代人的变动不居,这种风格在《花样年华》特别版的最后五分钟也可以看得出来。
不过,《花样年华》可以算得上是王家卫创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选择了李屏宾作为电影的主要摄影师,镜头变得静止且沉静,整部电影几乎都是小景别,让人物始终有一种被框住的感觉,既突出了角色生活空间的狭小,也反映了他们内心的禁锢感。
一定程度上,李屏宾的摄影让镜头始终在凝视着片中的人物,因为他们的情感非常压抑,我们需要利用特写才能感受到人们内心的隐秘。比如有影评人指出,这次重映在大银幕再看《花样年华》,才意识到两个人分别之际,苏丽珍用一只手抓着胳膊,指甲已经深深地嵌入肉中,这传递出一种因分别而产生的痛感,而这种感受是观众在小屏幕观看时难以体会的。
当然,《花样年华》也延续了王家卫的母题,依然是一部充斥着时间和身份焦虑的电影。周慕云和苏丽珍关系的突破是因为对武侠小说的热爱,而对香港这座城市来说,武侠小说链接的是这些内地移民与国族历史、民族大义的关系。至于他们总是在宾馆里相约写作,门牌号给出的“2046”四个数字,也有着很特殊的意义。在《花样年华》之后,王家卫继续拍摄周慕云的故事,这一次电影的名字就叫《2046》。
在这部“续作”电影中,“2046”成为科幻小说中列车将要驶去的地方,周慕云用自己小说主人公的独白告诉观众:“去2046的乘客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找回失去的记忆。因为在2046,一切事物永不改变。没有人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因为从来没有人回来过。我是唯一的一个。”在新的故事中,周慕云不再是那个深情款款的角色,他变成了一个伤害女人的浪子,尽管内心无法忘记过去,他也终于接受过去的不会再回来。在《2046》后,王家卫不再执迷于香港的过去,开始讲述一个发生在故土的故事,于是有了《一代宗师》。
2023年12月底,王家卫改编自金宇澄同名小说《繁花》的剧集上线,这也是他的作品第一次完全脱离香港这座城市,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上海。剧中的宝总和汪小姐最终也没有在一起,留给彼此一个潇洒的告别。时隔一年后,王家卫没有忘记要为《繁花》做一次“售后服务”,拍摄了一条关于《繁花》的短片。
原来,2000年《花样年华》在内地首映的时候,宝总和汪小姐都去了大光明电影院,并且再度重逢,这一次他们或许不会再错过。
很少有导演会如此善于利用自己的往日素材,也总能让影迷心甘情愿地埋单。虽然也有人质疑王家卫“炒冷饭”,但喜欢他的人却总是希望这位“墨镜王”可以再回片库拿点新东西放给大家看。不管如何,能够在大银幕反复观看《花样年华》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它证明了影院永远有它的魅力,电影里爱情才可以永远保鲜。
###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