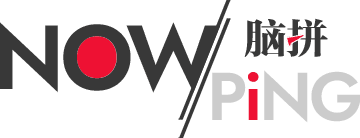孙立平:面对令人错愕的现实 重温亨廷顿远见卓识的五大预言
文/孙立平
1993 年《外交》季刊夏季号发表了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他在文中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三年后,亨廷顿出版了《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对该理论进行了系统地阐述。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当时引起极大的争议。要知道,当时正是冷战结束全球化刚刚起步、他的学生福山已经满怀信心地宣布历史已经终结的时候。就当时的氛围来说,亨廷顿的理论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在晴朗的全球化天空下显得是多么的阴暗。
但仅仅30年的时间过去,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令无数人错愕的现实。现在再回过头去看亨廷顿的一些预言,其远见卓识,真的令人惊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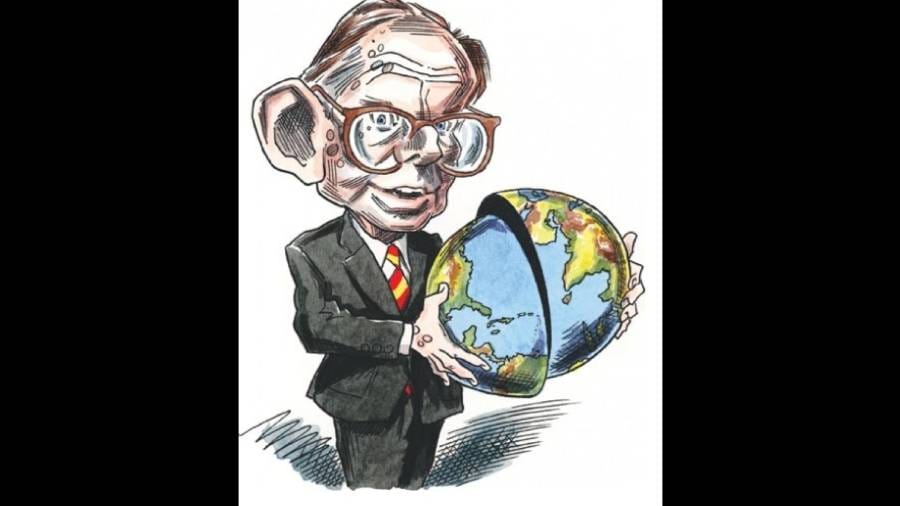
国际贸易带来好处,但也常常令彼此害怕,造成冲突
经济增长改变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均势,造成了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政治不稳定。经济交往可以使人们互相接触,但不能使他们达成协议。
在历史上,它往往使各国人民更深刻地认识到他们之间的不同,令他们彼此害怕。国家之间的贸易不仅带来了好处,而且也造成了冲突。
如果过去的经验靠得住,那么亚洲的经济成就将为其带了政治阴影,即不稳定和冲突。
在反复出现的美日贸易冲突中形成了一种模式: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对日本提出要求,并威胁说,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就进行制裁。接着就是无休止的谈判,然后双方在制裁生效之前的最后一刻宣布达成协议。协议的措辞通常是模棱两可的,因而美国可以宣布在原则上取得了胜利,日本则可根据自己的意愿执行或者不执行协议。于是一切照旧进行。
与中国的冲突也大体如此。中国勉强地同意在人权,知识产权和核扩散问题上的广泛的原则声明,但是对声明的解释去与美国极为不同,并且继续执行他以往的政策。
一点感想:具体的是非不说,在全球化与自由贸易洋溢的温暖和谐的氛围中,亨廷顿敏锐地预见到这种全球性贸易可能带来的摩擦与冲突,正在为今天的现实所验证。而所涉及的真正问题,还不仅仅是其中的摩擦与冲突,而是这种模式能不能长久地走下去。
西方极右势力崛起与移民问题相伴而生
西方文化受到了来自西方社会内部集团的挑战。其中一种挑战来自其他文明的移民,他们拒绝融入西方社会,继续坚持和宣扬他们原有社会的价值观、习俗和文化。这一现象在欧洲的穆斯林中最为显著,不过他们人数不多。
它在美国为数众多的拉美裔少数民族中也很显著,尽管程度较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同化移民的努力归于失败,美国便会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并存在内部冲突和由此造成分裂的潜在可能。
一个多文明的美国将不再是美利坚合众国,而是联合国……摒弃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实际上也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美国和西方的未来取决于美国人再次确认他们对西方文明的责任。
在美国内部,这意味着拒绝造成分裂的多元化注意的诱人号召。在国际上,则意味着拒绝要求美国认同亚洲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虚幻的号召。
欧洲和美国能够制止移民潮吗?……皮埃尔·勒鲁什总结道:“历史,亲缘关系和贫困使法国和欧洲注定要挤满来自南方不成功国家的人民。欧洲过去是白人和犹太教-基督教的欧洲,将来却不是”……问题并不在于欧洲是否伊斯兰化,或者美国是否拉美化,而在于欧洲和美国会否成为分裂的社会。这将取决于移民的数量和他们融入在欧洲和美国占优势的现有西方文化的程度。
一点感想:30年前预感的情景成了今天实实在在的现实。这个结果是什么?在几年前,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文明冲突的内部化。也许这就是今天困扰西方的最现实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现在似乎已经到了一个生死攸关的临界点。但我还是有点奇怪,他在书中为什么说欧洲穆斯林移民问题将在2025年解决?
穆斯林的边界是血腥的
在所有地区,穆斯林和属于其他文明的人——天主教徒、新教徒、东正教徒、印度教徒、华人、佛教徒金额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对抗性的,他们之间大部分在历史上的某一刻曾发生暴力冲突……沿着伊斯兰周边看去,穆斯林总是难以与其邻居和平相处。
文明间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战争。穆斯林的边界是血腥的,其内部也是如此。
伊斯兰起源于”好战的贝都因游牧部落”,伊斯兰教的基础深深地打上了这种暴力起源的烙印。穆罕默德本人就是作为一位坚强的战士和高超的军事指挥家留在人们记忆之中。(没有人会这样形容基督或者释迦牟尼)……《古兰经》和其他有关穆罕穆德信仰的陈述几乎都不禁止使用暴力,在穆斯林的教义和实践中没有非暴力的概念。
基督教主要通过使人皈依来传布,而伊斯兰教可以通过使人皈依和人口繁殖来传布。20世纪80年代基督教徒在世界上的人口比例达到约30%后稳定下来,现在开始下降,到2025年可能占世界人口的将近25%。世界上穆斯林人口由于极高的人口增长率,将继续急剧增长,大约在世纪之交达到世界人口的20%,再过若干年后将超过基督徒的人数,而到2025年可能占到世界人口的大约30%。好战,不相容,以及与非穆斯林群体相邻,仍然是穆斯林持续存在的特点,而且是造成整个历史过程中穆斯林具有冲突倾向的原因。
一点感想:血腥的伊斯兰边界,这句话,在1993年《外交》季刊上的那篇文章中就出现了。亨廷顿自己也承认,没有一句话比这句话招致更多的批评了。他的自我辩护是,大量不带偏见的资料完全证明了它的正确。我想,目前中东地区的冲突可能会提供更有力的佐证。
西方文明的价值在于其是独特的,而不是普世的
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机会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西方人眼中普世主义,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
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由于美国是最强大的西方国家,这个责任就不可推卸地主要落在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肩上。
但基督教国家具有一致对外的悠久传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美国既不可能统治世界也无法逃避世界。不论是国际主义还是孤立主义,不论是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都不能很好地为美国的利益服务。
只有避免这些极端的做法,采取与欧洲伙伴紧密合作的大西洋主义政策,保护和促进大家共同拥有的、独一无二的文明的利益和价值观,才能够最有力地促进美国的利益。
一点感想:这一段话不太好理解,但却非常重要。近来很多人脑子里都有一个很大的问号:特朗普毫无忌惮地拆除原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他究竟想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新秩序?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上面这段话中。简而言之,在过去美国领导人的脑子里的是一幅全球图景,美国来改造这个世界并领导这个世界。而亨廷顿的看法不同。他认为,西方文明的价值不是普适性的,不能拿它来改造世界;西方现在也不具备这个力量;西方能够做的是,把这种独特的文明保存下来,而这就是美国的责任;为此,需要有一个只是作为世界一部分的西方文明的圈子。如果这样来看,是不是可以看出点眉目来?
中美冲突不可避免
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和多元化的。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上,任何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没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那样至关重要。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中仍以现在的速度发展,那么中国将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以前在东亚的霸权地位。
美国与中国几乎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没有共同目标,两国的分歧是全面的。在最广泛的层面上,盛行于众多亚洲社会的儒家精神强调这样一些价值观:权威、等级制度、个人权力和利益居次要地位、一致的重要性、避免正面冲突、“保全”面子、以及总的说来,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
此外,亚洲人倾向于以百年和千年为单位来计算其社会的演进,把扩大长远利益放在首位。
这些态度与美国人信念的首要内容形成了对照,即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主义、以及美国人倾向于不信任政府、反对权威、赞成制衡、鼓励竞争、崇尚人权、倾向于忘记过去、忽视未来、集中精力尽可能扩大眼前的利益。冲突的根源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
不论亚洲和美国社会之间存在怎样的经济联系,根本上的文化差异将使二者无法同居一室。
亨廷顿甚至说,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尽管在宗教,文化,社会结构,传统,政治和根植于其生活方式的基本观念上,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但在政治上,共同的敌人将产生共同的利益,因此他们有理由彼此合作来反对西方。
一点感想:这些年,对中美之间可能冲突的讨论,主要是建立在修昔底德陷阱的假设基础上,即收成者与挑战者的关系。亨廷顿的理论有这个影子,但又不限于此,他更多强调的是西方与亚洲的价值观的差异,强调的是这种差异的全面性。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其中有的内容是比较虚的。让历史来验证吧。
###
来源:力平坐看云起